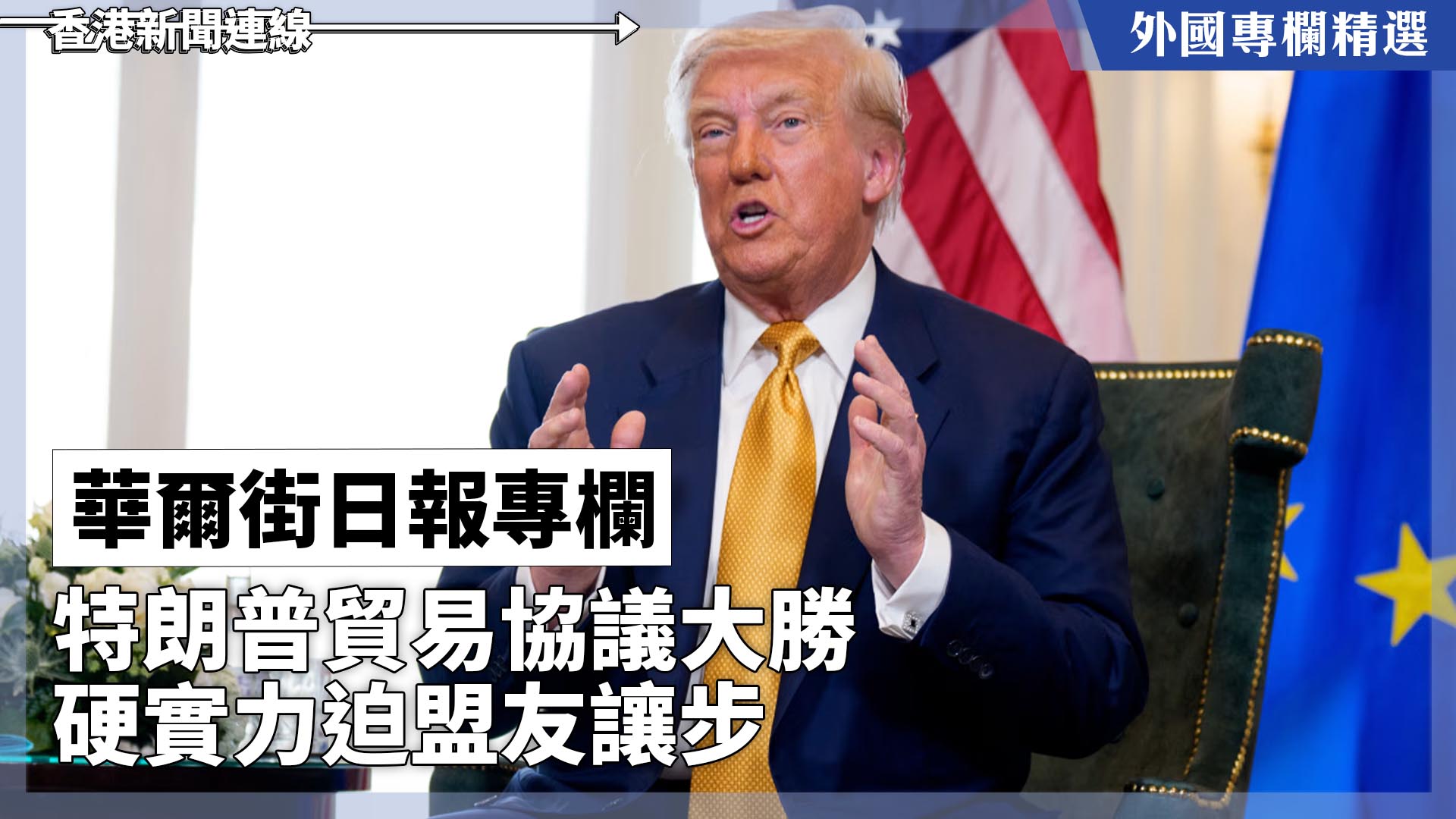
過去十天,特朗普總統敲定了多項貿易協議,若法院未判其大幅貿易權力違憲,這些將是他迄今最重要的成就。與日本及歐盟的協議顯示,主要貿易夥伴與關鍵安全盟友對特朗普政府要求作出重大讓步,卻未從美國獲得對等回報。
歐盟接受對美出口大多數商品15%的關稅,鋼鐵與鋁製品關稅可能更高,且不對美國產品報復。歐盟還同意大量購買美國能源與軍事裝備。
與日本的協議條件相似。除接受對美出口15%關稅外,日本同意投資5500億美元於美國,開放市場予更多美國農產品,並增加購買美國化石燃料、核能、民用飛機及其他高科技產品。
從特朗普團隊視角,這些協議證明其顛覆性策略的正確性。過去總統將安全關係與貿易談判分開,特朗普認為這愚蠢。他相信美國市場准入與安全保障的價值極高,外國會付出比前任總統更高的代價。與歐盟及日本的近期協議支持這一觀點。
特朗普還認為,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機構不如雙邊或區域協議更能服務美國利益。無需支持特朗普或關稅政策,也能看到世貿組織未達當初高期望。新的歐盟與日本貿易協議展現特朗普「分而治之」策略的潛力。
當然,這些協議的持久性與最終價值存疑。鑑於特朗普衝動撕毀舊協議(甚至包括他談判簽署的美墨加三方貿易協定),外國可能質疑他會否及多久遵守新協議。隨著其第二任期接近尾聲,外國政府對他的畏懼減少,或許會在履行承諾上打折扣。
特朗普政府貿易策略面臨其他障礙。挑戰其以緊急權力為由大幅改變關稅政策的合憲性訴訟正進入法院。關稅引發的價格上漲可能削弱公眾對保護主義貿易政策的支持。長期來看,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關稅扭曲激勵、引導投資至低效用途、減緩增長。他們還指出,從條約規定的貿易協定轉向不約束後任總統的行政協議,本身會增加風險、抑制跨境投資。
特朗普式外交與現實政治對聯盟體系的長期影響也引發疑問,這些體系歷來重視國際生活的穩定與價值觀。特朗普似乎認為,傳統盟友對美國的經濟與戰略依賴將使其繼續與美結盟,即使不滿美國作為。丹麥未因特朗普對格陵蘭的威脅退出北約;日本未因新關稅而倒向中國。
一些人認為,長期來看,失望的美國盟友可能尋求戰略獨立或與對手結盟,但這似乎不太可能。俄羅斯侵略與中國掠奪性貿易及安全政策,讓特朗普更強化美國聯盟。
但這些是未來憂慮。目前,即使反對特朗普貿易政策長期後果的人,也能從其成功中汲取教訓。數十年來,美國總統試圖說服盟友分擔更多責任、開放市場,卻無成果。
然後特朗普橫空出世,打破規則、粉碎常規。六個月後,除西班牙外,美國北約夥伴及台灣均增加國防開支。日本採取更積極政策,儘管特朗普政府調整貿易條件。在黑暗危險的世界,即使美國最自由主義與民主導向的盟友,也遠比價值觀共鳴更重視硬實力與經濟利益。
特朗普或許不會很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,但他正教授一堂關於美國盟友真實動機與優先事項的精彩課程,其後任若忽視,將自承風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