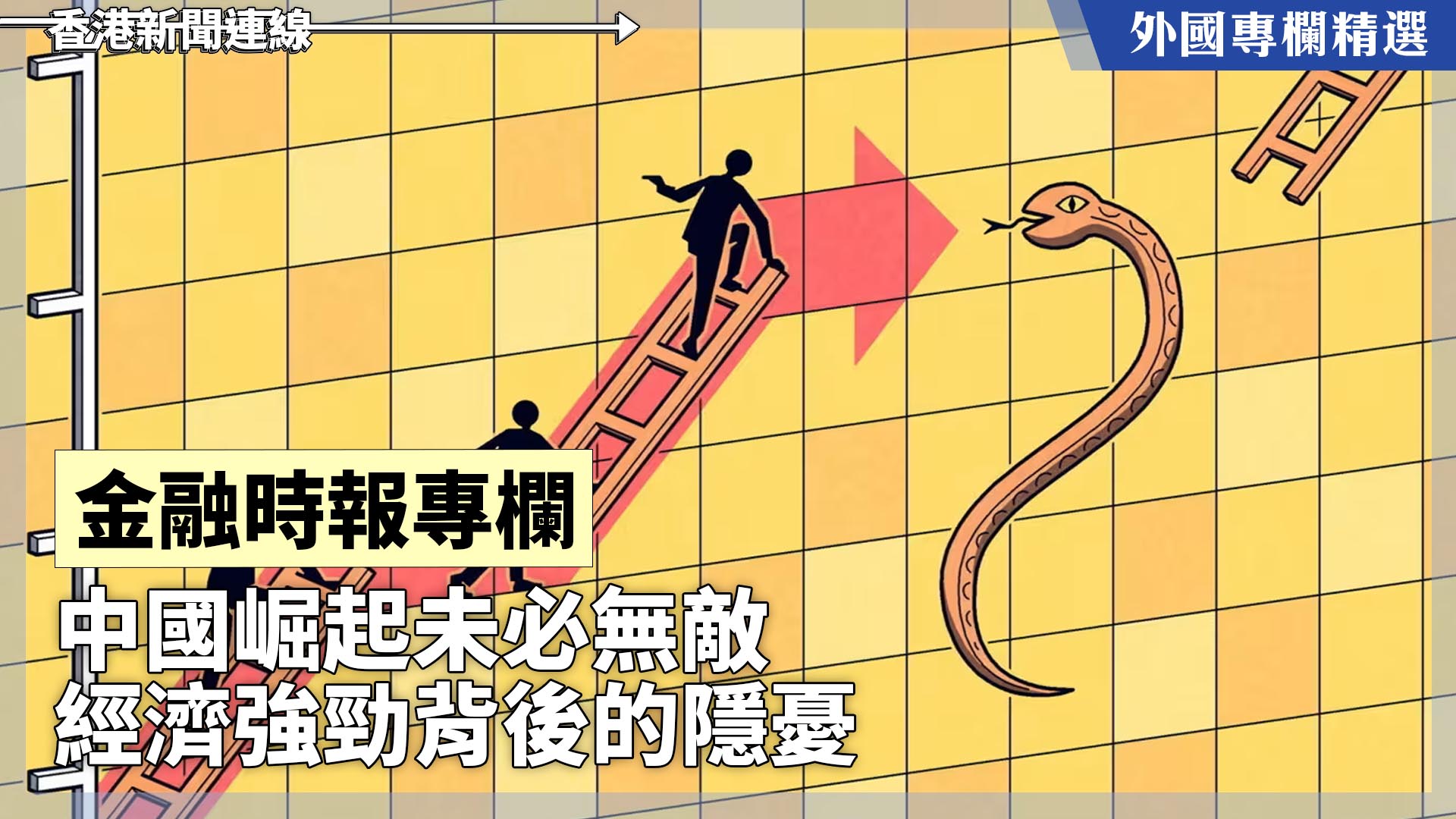
作者一向性格反叛,對任何一面倒、冇懷疑空間嘅說法都會保持警覺。無論係人工智能嘅興起、關稅嘅「惡魔化」,又或者近年愈嚟愈多人講中國將會無可阻擋咁崛起成為全球霸主,作者都習慣去質疑。
最近幾個星期,唔少投資者幾乎全盤接受咗呢個關於中國崛起嘅論調。北京似乎喺貿易戰中勝出,亦準備喺晶片戰同人工智能戰中再下一城,令中國成為新一代全球主導力量似乎已成定局。不過,呢個故事背後仍然有好多要留意嘅細節。
先講中國支持者最樂見嘅部分——中國嘅經濟引擎確實強勁,長遠產業規劃亦令人佩服。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強硬手段,北京喺稀土資源、農產品採購、以及尖端科技研發方面都展示出強大實力。正如英偉達行政總裁黃仁勳所講:「中國會贏喺人工智能賽道上。」中國亦善用美國嘅孤立主義傾向,積極喺東南亞、非洲同拉丁美洲建立新橋樑。
不過,壞消息係,呢啲努力都未能改變中國面對嘅根本挑戰——特別係如果佢真係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強國。單單以下三個現實,就足以令過度樂觀嘅想法降溫。
第一,雖然北京再三承諾要推動消費升級,但要喺數學同政治層面上達成呢個目標依然極為困難。第二,喺全球外交戰場上,北京的確獲得咗更多主動權,但實際成果遠少於理想。第三,專制體制喺全球依然難以被接受,令中國要取代美國甚至歐洲嘅軟實力地位變得更加艱難。
中國經濟要實現根本轉型,就必須真正落實以消費為主導嘅增長模式。不過呢樣嘢多年嚟都未實現,因為咁做意味住要將財富由地方政府、國有銀行同國企轉移到普通民眾手上。
呢個改變將會撼動整個政治經濟結構同既得利益,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。喺而家呢個時勢,呢種改革更加唔可能出現,因為習近平嘅議程重心放喺自給自足同對供應鏈嘅更大控制上。
中國最新五年計劃提出要通過科技自立、產業升級同擴大內需嚟達致「高質量發展」。作者認為,前兩項中國應該可以做到,但正如經濟學者佩蒂斯同政治學者伊康美指出,收入同就業增長唔可能靠自動化製造業,因為越嚟越多機械人取代人手,而係要靠市場力量去提升家庭消費,呢個就要求結束長期嘅金融壓制。
然而,現實上情況似乎相反——國家繼續派發補貼,例如人工智能晶片嘅新補助、消費疲弱、而多餘產能唔再出口美國,就被傾銷去歐洲市場。
講到第二個重點:特朗普削弱跨大西洋聯盟,本來俾咗中國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去拉攏歐盟。中國外交官本可以喺布魯塞爾大展拳腳,建立新貿易夥伴關係、整合價值鏈,甚至向歐洲保證會解決「中國廉價貨太多」嘅問題。
但事實係,問題根本冇解決——唔單止因為中國嘅經濟模式冇變,仲因為佢係俄羅斯嘅盟友同主要支援者,而俄羅斯正係歐洲最大嘅安全威脅。
喺呢種情況下,要出現所謂「歐亞聯盟」幾乎冇可能。即使美國對歐洲嘅承諾時有不穩(不過隨住上星期民主黨喺州及地方選舉獲勝,呢種不確定性似乎有所減少),歐洲亦難以完全轉向中國。
中國確實擅長搞重商主義,但喺「軟實力」方面遠遠不及。隨住科技同工業野心高漲,中國嘅國家控制反而越嚟越嚴。
而家嘅政治整肅係自毛澤東時代以嚟最嚴重。有人話反腐係其核心,而黨內會議上一啲空位顯示習近平確實喺清洗內部。不過,連策展人、藝術家、表演者、同記者都成為打壓對象,中國根本唔再係創意階層可以自由發揮嘅地方。
歷史上,全球霸權與開放性往往息息相關。經濟活力取決於人才同資本願意流入一個國家。不過自2015年以嚟,來自已開發國家嘅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中國減少咗七成,外籍居民簽證發出數量亦只回復至疫情前大約八成半。
雖然呢啲現象部分係因為地緣政治緊張,但即使環境改善,作者相信冇幾多跨國企業高層會將北京或者上海列為首選派駐地。呢啲問題未必會阻礙中國短期內嘅增長,但正正係任何一個有批判精神嘅人都應該深思嘅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