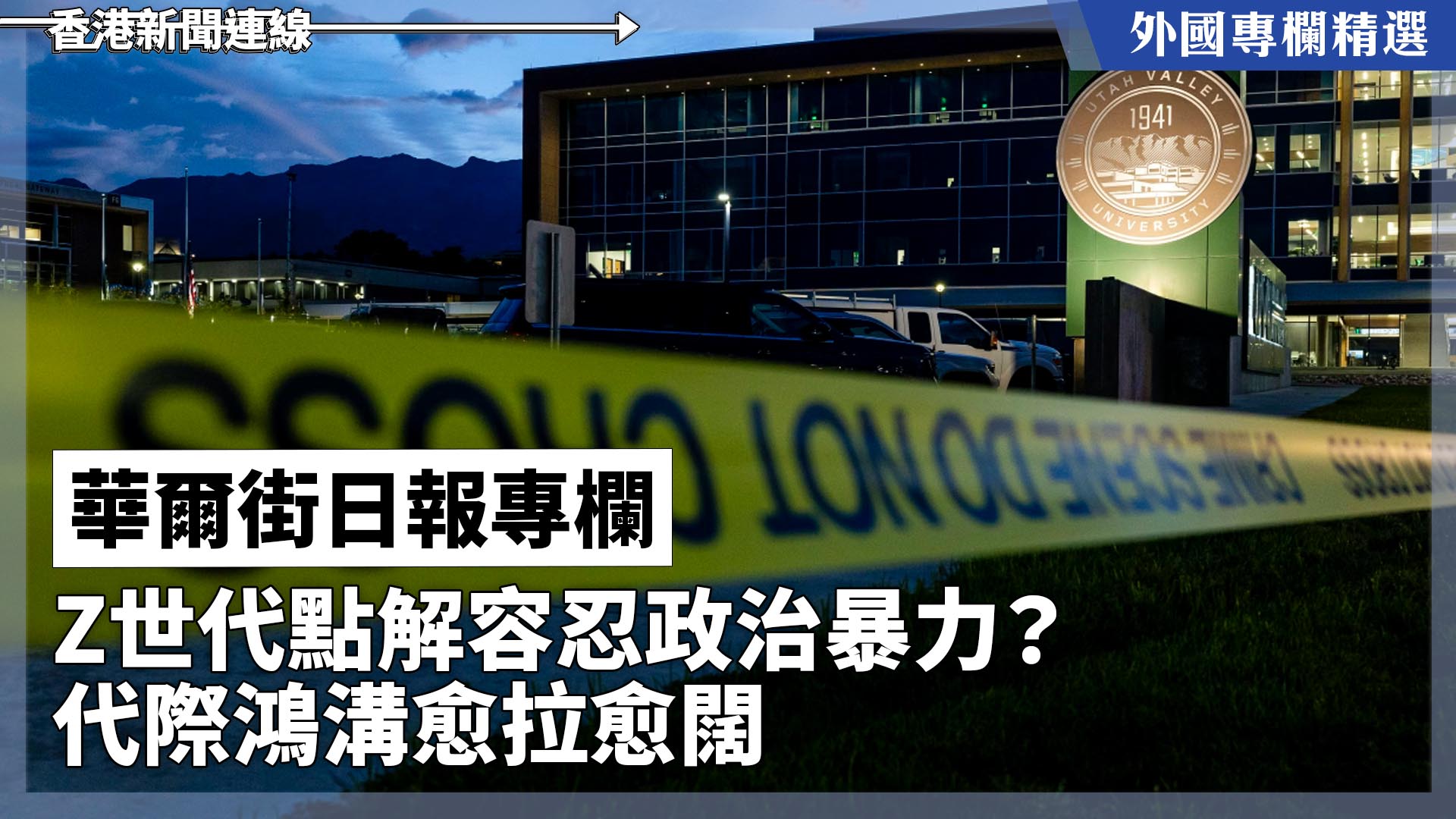
問美國人邊個要為近排嘅政治暴力事件負責,你會聽到兩個完全相反嘅答案。左翼會指向密芝根州州長韋特默綁架陰謀案、保羅·佩洛西遇襲、明尼蘇達州民主黨人梅麗莎·賀特曼同約翰·霍夫曼中槍,仲有1月6號國會山暴亂。右翼就會提起國會棒球練習槍擊案、聯合健康行政總裁白賴仁·湯普遜被殺、特朗普兩次遇刺未遂,仲有查理·柯克被暗殺。雙方都覺得對方先至係獨特嘅威脅,每次有新嘅政治暴力事件發生,都會迅速淪為黨派之間互數舊帳。
不過,最大嘅分歧唔喺意識形態,而係喺世代之間。「個人權利同表達基金會」嘅2026年大學言論自由排名顯示,而家超過三分之一嘅大學生認為「用暴力去阻止校園演講」係可以接受。呢個應該響起警鐘,無論喺課室、教員休息室,定係院長辦公室。
有人會傾向將責任推俾高等教育。過去十年,校園經常出現針對受邀講者嘅抗議活動,而大學領導層對政治包容重要性嘅表態往往模稜兩可。同時,學生不斷喺迎新資料、多元平等培訓、課堂同大綱中被灌輸一種觀念——言論等於暴力,而所謂社會公義之名嘅抵抗就被視為高尚。好多批評者認為,大學同學院其實係喺「教人不寬容」。
但實際上,支持用暴力去封殺言論嘅情況遠遠唔止於校園。筆者去年做過一次全國調查,受訪者睇到八句具爭議性甚至冒犯性嘅政治言論(例如「所有白人都係壓迫者」、「美國喺 9 · 1 1 得到應有嘅報應」、「1月6號其實係和平抗議」),然後揀出自己覺得最反感嗰句,再答「用暴力去阻止一場宣揚呢句說法嘅演講」係「絕不」、「很少」、「有時」定係「經常」可以接受。
好消息係,將近八成美國人拒絕用暴力去封殺自己唔鍾意嘅言論。民主黨人有77%、獨立派有80%、共和黨人有82%都認為暴力絕對唔可以接受。
壞消息係,分世代嚟睇就完全唔同。嬰兒潮世代有93%、X世代有86%認為暴力絕不可以接受,但千禧世代就只得71%,Z世代仲低至58%。而且,18至26歲嘅人,無論有冇喺大學讀書,睇法都冇乜分別。呢啲結果打破咗兩個迷思:唔係「敵人」先支持政治暴力,大學亦唔係唯一要負責嘅地方。
問題係,點解咁多後生會覺得,只要講嘅係「壞人」,就可以用暴力去阻止?有幾個原因同時出現:年青人嘅道德文化以一個極度寬泛嘅「傷害」定義為依據,將情緒安全放喺所有價值之上;社交媒體放大憤怒,令大家覺得「對面」總係可以僥倖過關;政治氛圍又鼓勵大家將對手視為必須消滅嘅威脅,而唔係需要說服嘅同胞。喺最冇依附於舊有自制同寬容規範嘅一代,反對暴力嘅共識先至會最快崩潰。
Z世代對用暴力去噤聲嘅迷戀,可能只係一時。隨住時間過去,佢哋可能會變得溫和,亦會更懂得珍惜自由民主嘅脆弱。呢代人成長喺政治極度撕裂、經濟動盪、疫情同2020年社會騷亂嘅年代。當呢啲記憶逐漸淡去,佢哋有機會擺脫偏激。
但而家,國家急需領袖——無論喺校園、政府定媒體——去堅守一個核心自由主義理念:暴力永遠唔可以作為回應言論嘅手段。高等教育機構尤其要抗拒退縮,繼續提供有爭議嘅言論平台。大學應該藉住呢個危機,增加而唔係減少保守派講者嘅邀請。正如前白宮新聞秘書艾利·弗萊舍講:「學術界唔可以成為保守派嘅禁區……如果自由派主導嘅大學能夠主動伸出橄欖枝,和平歡迎右翼,對修補國家撕裂會有幫助。」
暴力係會傳染嘅,而呢種傳播威脅緊自由社會最基本嘅承諾:公民可以自由發言、集會、參與公共生活,而唔使驚。要有更加自由嘅未來,我哋必須教導同堅守「說服,而唔係強迫」嘅規範,特別係對最容易放棄呢種規範嘅Z世代。